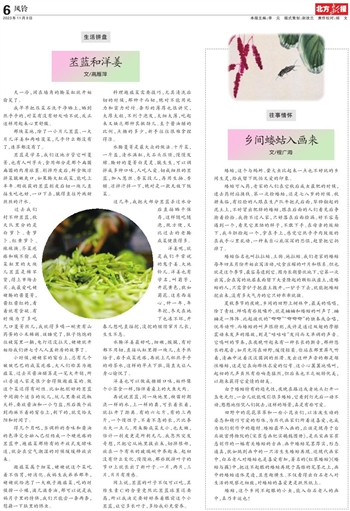蝼蛄,这个与蚂蚱、萤火虫比起来一点也不好玩的乡间生灵,给我留下既怕又爱的印象。
蝼蛄可入药,老家的人们在它秋后成虫最肥的时候,逮去药材站换钱。第一次捡蝼蛄,还是七八岁的时候。秋耕来临,有经验的人跟在生产队牛把式后面,犁铧翻起的泥土上,不时冒出肥胖的蝼蛄,跟在后面的人们看见后争抢着捡拾。我抢不过人家,只好落在后面捡漏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,看见它丑陋的样子,不敢下手。在母亲的鼓励下,我斗胆捡起一个,拿在手上,感觉它热乎乎肉鼓鼓的在我手心里乱动,一种来自心底深深的恐惧,赶紧把它扔掉了。
蝼蛄俗名也叫拉拉蛄、土狗、地拉蛄。我们老家的蝼蛄每年四五月份开始出窝活动,咬食庄稼的叶片和根系。但也就是这个季节,最容易逮到它。因为长期蛰伏地下,它第一次出窝,会在窝的地层表面留下大量隆起的颗粒状虚土,逮蝼蛄的人,只需拿铲子把虚土拨开,一铲子下去,就能把蝼蛄挖出来,没有多大气力的它只好乖乖就擒。
夏秋季节的夜晚,乡间的田野上树林中,最美的鸣唱,除了青蛙、蝉鸣有些鼓噪外,就是蛐蛐和蝼蛄的叫声了。蛐蛐是一阵阵、此起彼伏的“唧唧”“唧唧唧”的独奏或合唱,悦耳动听。而蝼蛄的叫声很特别,或许是通过双翅的摩擦震动来发声的缘故,则是“咕咕咕”发闷而又单调的声音。它鸣叫的节奏,在夜晚听起来有一种长长的颤音,那种悠长的尾音,如月光泻在田野,缓慢轻柔。你站在那里屏气听着,清幽中泛着淡淡圆润的丝滑。发出这种声音的都是雄性蝼蛄,这是它在向雌性求爱的信号。这小心翼翼地鸣叫,起初的几声虽然有些响亮猛烈,但后来也不乏婉转优美,以期来获得它爱情的甜美。
由于蝼蛄特有的趋光性,夜晚在路边或者地头打开一盏电光灯,一会儿就能吸引很多蝼蛄,它看到灯光后一动不动,憨憨地任凭人们捉去,这样的场景,真是有些可爱。
田野中的花花草草和一些小昆虫们,以活泼生动的姿态和精巧可爱的形体,为历代画家们所着迷喜爱,也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题材。蝼蛄最早入画的,应该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宋崔悫画杞实鹌鹑图册》,是北宋画家崔悫创作的一幅有关蝼蛄的古画。画中蝼蛄笔墨厚实,形态逼真,犹如跳到画中的一只活生生蝼蛄再现。近现代画家中,白石老人对蝼蛄也是喜爱有加,著名的《红蓼蝼蛄》《蝼蛄与藕》中,把这不起眼的蝼蛄再现于高雅的笔墨之上,画中的蝼蛄通体灵透,且意趣横生。不仅看得出白石老人对生活的观察之细致,对蝼蛄的喜爱更是跃然纸上。
蝼蛄,这个乡间不起眼的小虫,能入白石老人的画中,真乃幸运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