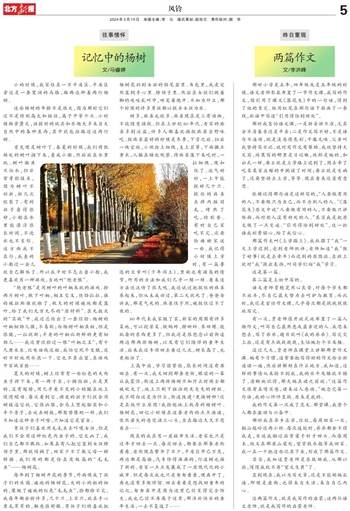小的时候,我家住在一片平房区。平房区旁边是一条宽阔的马路,路两边种着两行杨树。
这些杨树的年龄不是很大,因为那时它们还不是特别高大和粗壮,属于中等个头。小时候物资匮乏,孩提时的玩具和乐趣大多来自大自然中的各种东西,其中就包括路边这两行树。
首先便是树叶了。春夏的时候,我们将低矮处的树叶摘下来,叠成小船,然后放在水里玩。树叶船虽不怕水,但非常考验技术,因为树叶不耐折,折几次就裂了。有的孩子叠得很好,小船在水里能漂浮很长时间,不进水也不变形。这方面我不在行,我叠的小船过一会儿就自己解体了。所以我平时不怎么叠小船,我更喜欢另一种游戏,当地叫“尬老根”。
“尬老根”是用树叶的叶柄来玩的游戏。捡两片树叶,揪下叶柄,相互交叉,使劲拉扯,谁的被扯断谁就输了。秋天的时候遍地都是落叶,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“原材料”。在无数次的“实战”中,我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:杨树的叶柄韧劲儿强,不易断;白杨树叶柄虽粗,但是很脆,一拉就断;半老的叶柄比新鲜的更有韧劲儿……我还曾经捡过一根“叶柄之王”,有十几厘米长,比电话线还粗,我怕它风干变脆,还时不时地用水泡一下。它也不负众望,在游戏中百战百胜……
夏天的时候,树上经常有一些红色的大肉虫子掉下来,有一两寸长,小拇指粗,头是黑的,没有翅膀,用几乎看不见的小短腿在地上慢慢蠕动。每次看到它,调皮的孩子们就会用树枝逗它玩。它很凶狠,会马上竖起脑袋和小半个身子,去攻击树枝,那架势像蛇一样。我们不知道这种虫子叫啥,只知道它是害虫。
男孩子们喜欢用毛毛虫去吓唬女孩,但是我们不会用这种红色肉虫子的。它太凶了,我们自己都不敢抓。如果真有人把它塞到女孩脖领子里,那就闯祸了,回家少不了挨父母一顿胖揍。我们用的都是仿真度极高的“毛毛虫”——杨树花。
每年到了杨树开花的季节,外面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遍地的杨树花,大的小的粗的细的,像极了遍地的红色“毛毛虫”,捡都捡不完。我每年都会捡许多,几十只、上百只,放在手心里毛茸茸的,触感很舒服。男孩子们特喜欢把杨树花扔到女孩的铅笔盒里、书包里,或是突然塞到手心里、脖领子里。然后在女孩们跳着脚的吱哇乱叫中,哄笑着跑开。不知为什么,那个时候的许多男孩都以捉弄女孩为乐。
树多,麻雀也就多。麻雀现在是三有动物,不能随意捕捉。但在上世纪80年代,老家的麻雀多到泛滥,许多人都喜欢捕捉麻雀当野味吃。捉麻雀最好的时候是冬季,下雪之后。扫出一块空地,小棍拴上细绳,支上笸箩,下面撒点黄米,人躲在暗处观察。待麻雀落下来吃时,一拉细绳,便扣住了。运气好时,一上午能捉好几十只。捉住的麻雀去掉内脏羽毛,烤熟了吃,特别香。有时自己家吃不完,还要给姥姥家送一些。我记得小时候上学时,有一篇鲁迅的文章叫《少年闰土》,里面也有捕鸟的情节,所用的方法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。看来这方法还流传了很久呢。我还试过把捉住的麻雀养起来,但从未成功过,第二天就死了。爸爸告诉我,那是气死的。麻雀性子烈,被捉住过不了夜的。
80年代末我家搬了家,新家的周围有许多菜地,可以挖苦菜、捉蚂蚱、捞蝌蚪、养田螺。能玩耍的东西更多了,但我还是很想念以前街道两边那两排杨树,以及有它们陪伴的童年生活。后来我还专程回去看过几次,树长高了,也更粗壮了。
上高中后,学习很紧张,很长时间没有再回去。有一次,我又回到那条老街,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:街道上两排杨树不知什么时候全都被砍光了,地上只剩下粗壮的光秃秃的树桩。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,街道改建?更换树种?还是其他什么原因?我捡起地上残存的杨树叶、杨树花,回忆小时候在这条老街的点点滴滴,怅然若失的感觉涌上心头,坐在路边久久不愿离去……
现在的我在另一座城市生活,老家也只是过年才回去一次。每次回去,都要去那条老街看看。老街现在繁华了不少,平房区早已不见,两边都是高楼,汽车停得满满的,行道树也换了新的。老家一点点发展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。但是每次我也只是匆匆看看,便离开了,再也没有多做停留。回去看看是想找回童年的记忆,匆匆离开是因为这里已经变得完全陌生,我也已经不再属于这里,那淳朴快乐的童年生活,一去不复返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