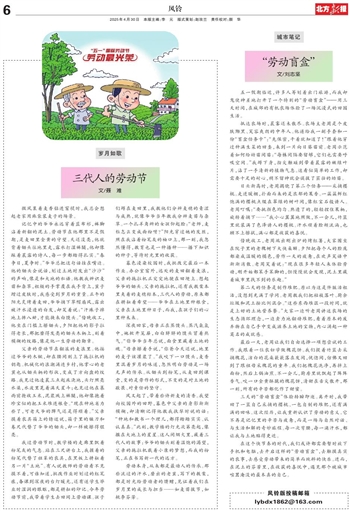微风裹着麦香钻进窗棂时,我总会想起老家用麻袋装麦子的场景。
记忆中的爷爷永远穿着蓝布衫,裤脚沾着新翻的泥土。劳动节在他那里不是假期,是麦田里金黄的守望。天还没亮,他就背着锄头往地里走,露水打湿裤腿,他却像踩着晨露的诗人,每一步都踏得扎实。“春争日,夏争时。”爷爷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他的锄头会说话,划过土地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像是和大地的私语。他教我辨识麦苗和杂草,粗糙的手掌覆在我手背上,茧子蹭过皮肤时,我感受到岁月的重量。正午的阳光炙烤着麦田,爷爷摘下草帽扇风,露出被汗水浸透的白发,却笑着说:“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,才能换来白馒头。”傍晚收工,他坐在门槛上擦锄头,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,那把磨得发亮的锄头木柄上,刻着模糊的纹路,像是他一生劳动的勋章。
父亲的劳动节在翻滚的麦浪里。他接过爷爷的木锨,却在腰间别上了拖拉机的钥匙。机械化的浪潮涌进乡村,他掌心的老茧也从锄头柄的形状,变成了方向盘的纹路。我见过他凌晨三点起床浇地,头灯照亮水渠,水波里晃着满天星斗;也见过他在暴雨前抢收玉米,泥浆溅上裤腿,他却像抱着珍宝似的把玉米堆进粮仓。“现在种地省力些了,可老天爷的脾气还是得顺着。”父亲摸着农具箱上的锈迹说,箱子里的镰刀和卷尺代替了爷爷的锄头,却一样被擦得锃亮。
我过劳动节时,教学楼的走廊里飘着粉笔灰的气息。站在三尺讲台上,我握着的粉笔代替了祖辈的农具,在黑板上耕耘着另一片“土地”。有人说教师的劳动看不见摸不着,可谁知道,批改作业时划过的红笔痕,备课到深夜的台灯暖光,还有送学生毕业时湿润的眼眶,都是耕耘的印记。今年劳动节前,我带着学生去田间上劳动课。孩子们蹲在麦田里,我教他们分辨麦穗的青涩与成熟,就像爷爷当年教我分辨麦苗与杂草。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仰起脸:“老师,麦粒怎么变成面粉呀?”阳光穿过她的发丝,照在我沾着粉笔灰的袖口上,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,教育也是一种播种——播下知识的种子,等待时光里的收获。
暮色浸染校园时,我批改完最后一本作业。办公室窗外,远处的麦田翻着麦浪,父亲的拖拉机正突突地驶在田埂上。想起爷爷的锄头、父亲的拖拉机,还有我教案本里夹着的麦穗标本,三代人的劳动,原来都在耕耘着希望——爷爷在土地里种粮食,父亲在土地里种日子,而我,在孩子们的心里种未来。
深夜回家,母亲正在蒸馒头。蒸汽氤氲中,她掀开笼屉,白白胖胖的馒头冒着热气。“你爷爷当年总说,面食里藏着土地的魂。”母亲擦着手说,“你爸今天还说,地里的麦子该灌浆了。”我咬下一口馒头,麦香里混着岁月的味道,忽然明白劳动是一场无声的传承。从锄头到粉笔,从麦田到课堂,变的是劳作的形式,不变的是对土地的敬畏、对责任的坚守。
风又起了,带着些许新麦的清香。我望向校园外的田野,暮色中父亲的身影渐渐模糊,却清晰记得他教我扶犁时说的话:“种地和教书一个理儿,都得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。”此刻,教学楼的灯光次第亮起,像撒在大地上的星星。这人间烟火里,藏着三代人的故事:爷爷的锄头刻着温饱的渴望,父亲的拖拉机载着小康的梦想,而我的粉笔,正在书写新一代的远方。
劳动本身,从来都是最动人的传承。那些流过的汗水,磨出的老茧,写下的教案,都是时光给劳动者的馈赠,见证着我们在岁月里的成长与担当——如麦苗拔节,如桃李芬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