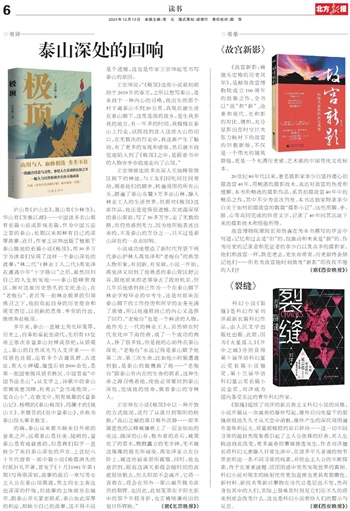多年来,泰山一直被主角光环笼罩,历史上,自秦始皇起至清代,先后有13位帝王依次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;从景观上,泰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并重——不仅景色壮丽,还有多个古建筑群、古遗址,有大小碑碣、摩崖石刻2000余处,是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中国首座“中国书法名山”;从文学上,诗歌中的泰山常被寓意顶峰,杜甫云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在散文中,则有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、杨朔的《泰山极顶》、冯骥才的《挑山工》、李健吾的《雨中登泰山》,并称为泰山四大著名散文。
的确,泰山从来都不缺来自外部的誉美之声,远观泰山是壮美、陡峭的,登泰山是有成就感的,但是我们似乎一直缺少了来自泰山深处的声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部中篇小说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(礼平著,首发于《十月》1981年第1期)写得很深刻,故事的最后一章写男女主人公在泰山顶偶遇,男主向女主表达出深深的忏悔,但故事的主体部分在城市,跟泰山并无紧密联系。泰山如此深厚的积淀,却缺少自己的故事,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,这也是作家王宗坤起笔书写泰山的原因。
王宗坤说:“《极顶》这部小说最初萌动于2019年的春天,之所以想写泰山,是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召唤,我出生的那个村子离泰山不到20公里,我现在就生活在泰山脚下,这里是我的故乡,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有一年多的时间,我慢慢在泰山上行走,试图找到进入这部大山的切口,在无数次的行走中,我逐渐产生了触动,有了更多的发现和感悟,然后就不自觉地陷入到了《极顶》之中,是跟着书中的人物亦步亦趋地走向了山顶。”
王宗坤曾连续多次深入天烛峰管理区辖下的林地,与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循着他们的脚步,转遍周围的所有山头,踏遍了泰山东麓3万多亩山林,融入林业工人的生活世界。但面对《极顶》这部作品,他还是觉得很遗憾,在底蕴深厚的泰山面前,写了30多万字,走了无数的路,但仍然感到无力,因为他所能表述出来的,不及泰山的万分之一,只不过是泰山深处的一点点回响。
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新时代背景下两代泰山护林人禹奕泽和“老炮台”的典型人物形象,有创新、有突破。小说一开始,禹奕泽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泰山管区舒云谷,跟他原来的老领导去了政府机关,但几年后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在泰山脚下林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,还是对原来在泰山脚下的工作经历和所学的业务充满了感情,所以他遵照自己的内心又选择了回归。“老炮台”也是一个鲜活的人物,他作为上一代的林业工人,虽然曾在时代变化中下海经商,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,挣了很多钱,但是他的心始终在泰山深处。“老炮台”永远记得是泰山赋予他第二次、第三次生命,比如他小时候遭遇到狼,是泰山的雄鹰救了他——“老炮台”跟泰山有内在的生命的联系,这种生命之源召唤着他,使他必须要回到泰山深处,完成他的使命,做着泰山的守林人。
王宗坤在小说《极顶》中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收尾,进行了从落日到朝阳的转换:“高山之巅的落日格外沉静……原本黛蓝色的云峰被镶嵌上了一层金灿灿的亮边。幽深的山谷,散布着的奇石,被简化了的草木,默默矗立的无字碑,无不被这璀璨的霞光所浸染。禹奕泽呆立在台阶上,被这壮丽美景所震慑。同时,他也意识到,眼前这满天彩霞会随时间的流逝很快散去,但太阳却不会离开,它将一直都在,将会在另外一面山巅升腾为浓烈的朝晖。也因此,此刻笼罩在夕阳光影中的那个年轻身影,也正被喷薄而出的旭日所辉映。”(据《北京晚报》)